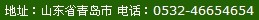|
新片上线 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与各种传染病的斗争史。 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黑死病”夺走了至少万人的生命,让整个欧洲陷入恐慌。但直到约年后,法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发现了这种瘟疫的病原体——耶尔森氏鼠疫杆菌,人们才算是真正找到了对抗“黑死病”的方法。 在现代技术手段下,想找到某种传染病的病原体,已经不用再等几百年。 还记得“非典”吗?从疫情开始到确认病原体,我们用了近5个月; 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更快,8天时间就确定了病原体。 争分夺秒,但似乎又永远比传染病“慢半拍”——为什么在传染病面前,人类总像是在开“马后炮”? 我们不知道 哪一个传染病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 很遗憾,在这个问题面前,人类的回答一般是:我们不知道。 这也导致长久以来,人类的传染病防控研究,通常是这样的:疾病出现后,探寻并明确病原体,继而开展对传播途径、流行特点、动物宿主、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工作。人们称之为“马后炮”,期望能够提前、再提前。 可现实明摆着,至今唯一被消灭的传染病只有天花。像流感、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狂犬病、麻疹等依然影响着人类健康。而《自然》杂志曾指出,在世界新发传染病中,人畜共患病占60%,其中71.8%来自野生动物。学界的共识则是,“人畜共患病难以预测”。 有多难?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做过系统研究,他和团队发现,喜马拉雅旱獭的粪便中,97%以上的细菌都是未知的;99.8%的藏羚羊粪便的细菌也从未被明确知晓。潜台词,是否对人类具有危害,能造成多大危害——还得去证明。 至于到底能证明多少,能在传染病突发之际争取多少时间,这也是徐建国一直努力在做的。 “无心插柳” 年,已经是卫生部分子医学细菌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的徐建国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就听到一个非常急切的声音说:徐教授,你出趟差吧,去徐州。 徐建国有点懵:让我去徐州做什么? 但电话那边的人怎么都不肯透露,只是反复强调:任务保密,请他尽快到徐州协助调查。 直到上了火车,徐建国才从乘务员口中探知,徐州爆发了一种传染病,正在死人呢! 徐建国慌乱。这是刚下火车的徐建国,对徐州的第一印象。 这次的传染病来得很凶险。 很多病人一开始只有拉肚子的症状,医生们也都是按拉肚子的方法治疗的。但就在大家觉得病人症状减轻的时候,被感染者会突然出现少尿或无尿的症状,然后迅速因急性肾衰死亡。 整个徐州因为这场传染病人心惶惶。当地卫生部门相关检测也做了,病菌也找了,但始终不能确定导致这次传染病的病原体是什么。 徐建国仔细研究了一下现有的病历,很快就在疫情讨论会上笃定地指出:导致这次传染病的,就是大肠杆菌O:H7(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概述图他对这种病菌很熟悉。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徐建国跟着导师研究的就是它。他甚至还创造性发展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诊断探针。 虽说一开始,这种病菌的主要爆发地集中在欧洲,很多人都觉得亚洲不可能有这种病菌。但徐建国却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即便回国,也一直没停下对这方面的研究。 当初的无心之举,给徐州帮了大忙。徐建国贡献出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疫情很快被控制住了。 有的放矢 徐州一战后,盘旋在徐建国心里的一个想法,慢慢清晰起来。 一般来说,当某个地区爆发出一种烈性传染病,各个部门的应对策略基本都是先以隔离为主,根据感染者的症状摸索治疗。等研究人员找到这次疫情的病原体,才能根据病原体的特点对症下药。 但找病原体的这个过程,时间不太可控。 徐建国在实验室研究人员不能直接从病人的体内找到病原体,尤其是在一种新发传染病面前。 他们往往需要先经过分离、培养、纯化、鉴定几个步骤,使病原体达到一定数量,才能满足做后续实验的条件。可实验也未必每次都能顺当,这一等,说不定几天甚至几个月就过去了。 徐建国觉得,徐州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之所以能够早诊断、早控制,还是因为有过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储备。 怎么储备?按经验来看,一般能导致大规模传染病的病原体,大多都和野生动物有关。而那些和人类活动接触密切的野生动物,就成了徐建国脑海里的首选研究对象。 经过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徐建国和同事们定下了一个包含80多种罕见病原菌储备名录。他们要从这份名录入手,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做研究储备。而这,就是后来他一直在推崇的“反向病原学”理念。 徐建国(右)和同事在青藏高原做调研/截自《我是科学人》纪录片让徐建国高兴的是,他们的储备还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年,四川爆发了非常严重的猪链球菌疫情,导致人被感染,死亡率高达17.6%。而这种病菌,徐建国正好让学生在1年前做过相关研究。所以,这次疫情,在很短时间内就被控制住了。 事实上,在和“不明原因性传染病”打交道的40多年里,徐建国经历过很多公共卫生事件:年山东发生的多细菌协同性坏疽、年四川德州星状奴卡氏菌注射感染事件、年人工饲养果子狸携带SARS病毒调查、年安徽人粒细胞无形体病院内传播、年玉树地震灾后鼠疫防控等。 经历越多,他对“储备”这件事就越在意。他知道,在自然界数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的已知、未知的微生物面前,他们的力量非常渺小。可他更知道,越多的病原体被“看到”、被“了解”,新发传染病爆发时,就有可能为之提供更多的线索,让人做出更快的判断,使更多生命得到挽救。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徐建国曾带着团队在非典时期跑遍全国14个省的果子狸养殖场,也曾登上青藏高原研究旱獭、秃鹫、藏羚羊、鼠兔、藏野驴。年复一年,他们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分离、命名了50多种新细菌、新病毒——当初那份简单的名录正被编织成网,并且还在日益扩充。 只要能够为潜在的传染病防控提供支持,每多发现一种都是好的——徐建国心想。 《我是科学人》纪录片由长安信托特约赞助。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fydgt.com/jbjc/12800.html |
当前位置: 肠结核疾病_肠结核疾病 >罕见病菌突袭中国,幸亏他提前开展了研究
罕见病菌突袭中国,幸亏他提前开展了研究
时间:2023-2-1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肺炎是怎么引起的肺炎应该怎么治三九养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